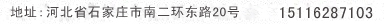请你一定要耐心看完癌症不等于死亡上
年,我流年不利,从开春就住院,至今方初离病榻。这一年来,在死神的门口徘徊,我接触到了多少生离和死别;多少眼泪与悲伤;多少痛苦与折磨啊!也许是死神的庭院狭窄,世界在这儿浓缩了。也许死亡毕竟是最后裁决,一切人在这儿都洗尽铅华,扯去了纱幕,呈现出赤裸裸的灵魂。于是,忠贞与负义,廉洁与贪婪,坚强与怯懦,善良与残忍,崇高与卑鄙……一切人的本性在这里都纤尘俱显,须眉毕露,进行着淋漓尽致的表演。这一年来,我又看到了多少悲剧和喜剧,正剧和闹剧啊!事物原来确是一分为二的,我的流年不利反而使我眼界大开。本来,激动对病是有害的,会使病情加重或反复。但真诚的歌吟与愤怒,毕竟是对感情的净化和意志的磨练。因此,在年已半百时能进一步地透视人生,终归还是创作人员的大幸事。为了对救死扶伤白衣战士真心的尊敬,为了对顽强和死神角力的勇士的赞美,为了对一切善良和忠贞美德的歌颂,也为了对一切卑劣、残忍、负义和背弃行径的鞭挞……我有多少故事将向人们讲诉啊!但是,在这里,出乎我自己意料,也许也出乎读者意料,我却要首先给你们讲一个神话。一个古老的,却又是新奇的、不是神话的关于气功治癌的“神话”。 两个嫌疑犯首先声明:我对气功一窍不通,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我并且自命是个文明人,多少受过一点科学的教育,因此对还不能用科学理论全面阐述的气功,不免还有些轻视的心理。所以,这里所说,决不可能有任何门户之见。它只是一个普通病人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生活片断的客观报导而已。既是亲身经历,那么,还是得从自己谈起:年10月,我刚出院不久,由于休养得不好,心电图比住院时还糟……偏偏祸不单行,又突发大量无痛血尿,重又急诊入院,并且成了癌症的嫌疑犯。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既然有了嫌疑,就难免对此类病人格外留心起来。谁知,不留心还好,一留心,怎么?竟前后左右都是: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贲门癌、胰腺癌、结肠癌。直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哦,原来癌症病人这么多!而且由于病因至今不明,发展期几乎全无自觉症状,往往容易忽略,待到症状明显时,大都已是晚期了。可以说是一脚已迈进了死神的门槛,死亡率极高。因此,在癌病房内外,不但家属亲友愁肠寸断,医生护士特别肃静耐心;就连不相于的路人到此也都不禁敛气屏息,压低了声音说话,好一派肃杀景象。我既有幸涉嫌,自然,亲朋好友、组织、同志都对我格外亲切和蔼。不但四处奔走为我访医求药,而且不断笑语劝慰,其中不少人就一再提到了气功。由于我上述的无知和偏见,我在感激之余,总是笑着谢绝说:“气功吗?那是很深奥的东西,我这人很笨,怕是学不会的吧?我还是多吃点饭,准备体力,长瘤就开刀吧。”话虽如此说,但说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明白:心脏病患者接受任何手术都很麻烦,更何况癌?!但即使如此,我仍没想到需要进一步了解一下气功,桌上好几本有关气功治病、气功防癌治癌的小册子连翻也没翻。因为,不是癌便罢,万一是癌,时间可真是不多了。我得赶快把我手头的小说写完,要不然,两眼一闭,烂在肚里,岂不可惜!一天,一位坚持说我不像是癌的病友林研究员,突然到我房里来闲谈说:“你不是癌……不过,做做气功有什么不好呢?你看见9号的梅部长了吗?他是食道癌。70多岁,受不了开刀了,在配合放疗同时,他坚持做气功。3个月下来,不但经住了放疗,而且11公分的病灶,现在只剩7公分了。他很快就要出院,专门做气功去了……”之后,好像约好了似的,不少病友和我闲谈时都说:“你不是癌,不过气功……梅部长……”我终于注意起梅部长来了。是的,医院,我亲眼看到了化疗、放疗对病人体力的消耗。因为放射线和许多抗癌药物虽然杀伤癌细胞,但却敌我不分,也杀伤健康细胞和白血球。因此,很多病人很快就体力不支,倒了下去,于是死神就……而梅部长,虽然年逾古稀,却闯过了这关,不但肿物缩小,而且精神矍铄。数九寒天,风雪无阻,每天坚持在户外练功,不要说自己倒下,连六七级大风也刮他不倒……难道真是气功的作用?!我心动了一下,但仍然是偏见占了上风:也许是特异体质吧。我没有知识深究,也无暇多想,还是抢我的小说要紧。这样,就到了11月。一天,楼下23号的陈大姐来看我:“排除了吗?”她问:“还在一项项地检查。”“结果如何?”“待除外。”“气功的书看了吗?”像一切革命队伍中的老大姐一样,她总是对人那样亲切、关心。“还没有。”我抱歉地笑笑。“你隔壁新来了个同志,也是个嫌疑犯。不过他的嫌疑可比你大多了。”她突然降低了声音,“他脖子上都出现了肿块,而且不止一块……”“也许是淋巴结肿大吧。”我说出了每一个好心人在这种情况下必说的话。她摇了摇头,说:“他是专门到北京来学气功的,好像在南京已有过诊断。”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人可好啦,是我国最早的领航员之一,是我的一个老战友,也姓陈。一会儿我们去看看他!”可是没等我们去看他,吃过饭老陈就看我们来了。黝黑的面孔,壮壮实实的身材,哈哈大笑着,抢着说话,声音又响又亮,轰轰地震入耳鼓。“你哪里像个病人。”我说。“但愿和你一样,仅是个嫌疑犯。可是不行,脖子上出现好几个肿块,都连成一片了。”他一边伸出脖子让我们摸,一边还笑。“做过切片了吗!”我摸着那些比核桃都大的肿块,实在说不出那句宽心的话了,但仍满怀希望地问。“做了。他妈的,说就是那家伙。可又找不到原发灶。”我的心往下一沉。陈大姐赶忙说:“那可能就不是呗!你哪里像个病人。”“你真不像个病人。”不知为什么,我变得像个学舌的鹦鹉,明知道自己的话毫无意义。老陈却仍然轰轰大笑着:“像不像有啥?听说垮下来可快了。所以,趁还能动,我赶快到北京来学气功。”他翻着我桌上郭林的《新气功防癌治癌法》。“你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我……看不懂。”他就是上北京学气功来的,这是他的希望所在。我能说我不相信,我没看过吗?不,我不能。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有些遗憾,但仍轰轰大笑着:“那是因为对你,它的必要性还不像对我那么大。我,可是要争分夺秒了。我在南京就看了。我相信。我老婆现在正满北京找郭林呢!听说现在可不好找了……不过听说她办了一个癌症班,不少人治好了?!”他满怀希望地凝视着我们,好像要从我和陈大姐眼里探测出真假。我赶紧敛神静气,除了使劲地点头,还能说什么呢?过了几天,陈大姐告诉我:老陈的爱人好不容易找到了郭林同志,哪里只是一个癌症班,是好几个呢!分散在紫竹院、地坛等公园。她给我讲了好些个老陈爱人带回来的神奇的故事,无非是一些癌已广泛转移了的晚期病人如何绝处逢生的。她动员我也去学。我只是笑着不说话。她不知道,对我这个自命的文明人,越带神奇色彩,我就越不敢相信。而且三九天,大北风刮着,我连散步都不能出楼。上紫竹院去学气功,心脏病加重了怎么办?!医院也不同意我们去。我的情况如上述。陈大姐严重的糖尿病,正用着胰岛素,晕倒了算谁的?老陈呢?早就低烧,短短几天,已经开始了疼痛。出去学功?万一转成高烧,出问题是随时可能的。可老陈,他的家属,还有陈大姐都在拼命为他争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的检查结果全部出来了。经过研究,基本排除。于是病友们都向我祝贺,真心实意地为我高兴。走廊、饭厅里都能听到人们传说:解放喽,21号解放喽!我这才明白,原来从癌的王国里释放一个俘虏,哪怕只是一个嫌疑犯,都是一件多么不小的事情。而人的思维也真奇怪,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却是——唉!真正解放了,再也不用为去不去做气功进行思想斗争了。无巧不成书的是,恰在此时,17号老陈的CT结果也出来了:已在腹部找到了原发病灶,进一步确诊了他颈部的肿块全然无误地就是淋巴转移癌。我心里突然那样难过,好像很对不住老陈似的。昨天还是两个一道待判的嫌疑犯,今天却分道扬镳了。死神不知为什么暂时撇开了我,专心致志地向他猛扑了过去。还存在角力的可能吗?我马上去找了医生,悄悄地问她:“17号,还——有希望吗?”了解到我什么都知道了,医生垂下了眼皮,说:“尽力抢救吧。”“还——开刀吗?”“淋巴广泛转移,手术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明天就开始放疗。化疗……”“类似病例,有过救活的吗?”摇头。“那么,只是时间问题?”点头。“根据理论及临床经验,他……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医生犹犹疑疑地望着我。看着我恳求的执拗的神色,根据我的职业特点及对我的信任,她最后不情愿地、悄没声地翁动着嘴皮说:“一般情况这种病例……如果病人配合得好……两三个月吧。还没听说能拖过半年的。搞不好…当然…随时都可能……”如果配合得好?据我眼见,老陈可以说是个配合得最好的病人。他每顿吃两三个大馒头,喝两碗牛奶,中间还加餐,把他爱人送来的各种营养食物一律吃光。不论低烧使人多么乏力,疼痛多么难熬,他每天坚持两三次散步。他明明是咬着牙在和死神角力,可留给他的时间竟那么少,两三个月,还没听说有拖过半年的……我打了一个寒噤,突然觉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凉。“那你们还不让人去学气功!”我突然嚷了起来,“死马当作活马医嘛,人家原是奔气功才上北京来的呀……”“我们已经反映上去了,领导正在研究。这种情况,如果病人坚持——当然,要去还得安排车、陪同……”“你去领导那儿为他争取嘛!你就说,老陈爱人好不容易给他报上了名……你就说,陈大姐去。我也去。我们会彼此照顾的。何况,老陈的爱人是个最细心的陪同……”不知怎么,我突然为能让老陈去学气功苦苦地哀求起医生来,倒好像我原就是个气功信仰者一样。我后来回想:大概也就是在那时,我才下决心去认识气功这个陌生事物的。驾轻就熟,驾轻就熟,人,似乎总是习惯于走老路的。只有在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去开辟新路,向新的领域迈进。人们一向不愿意承认这种习惯为惰性,那么,应该叫它什么呢?!反正,不管怎样,我就这样一头撞进了气功的领域。 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们决定了去学气功,医院领导也批准了之后,我却失眠了。我从小就怕人哭;长大了怕人泣;历尽沧桑后,更怕的是无泪的绝望。这一次,进入了癌病区,我已看到了太多太深的痛苦,好像是绝大多数有去无回,即使手术顺利,也似乎只是假释,迟早要缉拿归案的。医院,总还穿插着别的病种,听得见轻病号的欢笑,也不断感染着痊愈出院病人的喜悦。这回可倒好,自投罗网要去癌症班,清一色的癌症病人。不说阴森恐怖吧,至少也是愁云惨雾……唉,唉,我可怎么受得了呢?!受不了也得受,这是自己苦苦哀求来的。莫不成还能打退堂鼓?不,不行,毕竟不是小青年了,硬着头皮往里钻吧。一进紫竹院的门,就觉得寒气逼人,呼呼的大北风卷着地下的沙土扑面而来,几乎站立不住。老陈和他的爱人满怀热情地到处打问郭林那个癌症班。我不知陈大姐作何感想,我呢?揣想着即将目睹成群挣扎在死亡线上人们的惨状,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心,缩得越来越紧。我带着硬摆在脸上的微笑,迈着机械的步子,厚厚的大衣被风卷了起来,好像是在旋风中沉浮的落叶。哦,冷!身心全是彻骨的冷。我不记得在我的一生中有过比这更冷的冬天。转过一座小土坡,眼前出现了一大片人,男女老少都有。一个年轻的军人站在一个石墩上,正在讲着什么。风把他的声音刮走了,我听不见。但人群却爆发了一阵响亮的大笑,想必他说了什么可笑的事,有几个穿红着绿的姑娘竟笑弯了腰。人群中还有几个现役军人,他们的笑声更是豪爽而雄壮。哦,究竟是些干什么的人呢?莫非这样大冷的天还有人游园?等报了名之后,女辅导员施柯同志领我们到班里去。走近这群人时,只听又是一阵哄笑,那位军人原来也不年轻了,四十左右年纪。他也大声地笑着,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想是怕人听不懂,句尾又撇着一点京腔:“咦,你们倒笑得开心哩!听别个做蠢事你们觉得好笑,自己咋样哩?想一下嘛,天天在和阎王老子打交道,又明明晓得做气功最怕生气,可有的人不加紧练功还要找气生,那不是明摆着给阎王老子送节礼吗?所以我说咹,要是哪个老癌默道斗不过了,索性安生当俘虏算了,又何必消费那么大事到前沿来资敌咧?……”我的脚步一下子停住了,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怎么,这就是那个癌症班?不,不像。癌症班还能有这样响亮的笑声?再说,哪有医生直管病人叫“老癌”的道理?也许,是些一般的慢性病人吧!好像为了证实我的疑惑,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军人,大声叫着“阿姨”,迎面向我跑来。哦,认出来了,这是我的两个青年朋友:小罗和小韩。那么,这些人,当然就不是那个癌症班的人了。小韩和小罗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亲热地问过我之所以到这里来的经过,爽朗地笑着说:“阿姨,排除了当然好,就是没排除,也不怕。你看这些人……”于是他们一个个地指给我看,说:“那个大声讲话的军人,叫于大元,是这班的辅导员。他自己就是个癌症病人,直肠癌。”我一愣,哦!“那个老太太,看见吗?就是脸儿尖尖的,头发雪白的,在那里张着嘴大笑的。对,就是那个,肝癌。70岁了,医生原说她活不过今年‘十一’的。”我又是一愣。哦,现在不是已经11月了吗?“你顺着我的手看,那边那个穿紫衣服的女同志,看见了吗?胸腺癌,两次复发,广泛转移,医生原说她活不过去年‘十一’的。再看那边那个胖胖的小伙子,肺癌,才26岁。”小罗突然降低了声音:“据说只有三四个月了。你回头,树边上那个和人逗笑的姑娘,看见吗?对,就是那个拉着别人头巾看花样的那个,才27岁,乳腺癌。手术后不到一年已广泛转移……”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她竟还有心思学织毛线花样?!“那边那个军人,对,就是正说话的那个,鼻咽癌。那个站得笔挺的,穿登山服的小伙子,对,就是那个,肾癌……”“怎么,怎么都是癌?”小韩和小罗一起笑了:“癌症班嘛!当然,有些是手术后防止转移,但大多是已经无法再行手术和接受放疗化疗的。也就是说:都是些被判处了‘死刑’的人。”我一愣,一愣,又一愣;至此,完完全全地瞠目结舌了。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们!是的,这个词多么确切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们说得多么轻松,而那些“死回”们也竟都那样沉着。看来,并不都是视死如归的哲人吧?恐怕更多的是下定决心和死神顽强角力的勇士。我忙指着老陈,悄悄地把他的情况告诉这两位小友,请他们快去讲给他听。但一定注意别透露出他自己还不知道的病情。两个青年向老陈轻快地跑了过去。一会儿,从他们那里就传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小罗的声音纯净甜美,像领唱的女高音;小韩的声音高亢而沉静,充满了力量和信心;而老陈呢,还是那样轰轰的大笑,就像乐队里的低音鼓,不但震入耳鼓,而且震撼人心。我突然觉得暖和了起来。哦,今年的冬天原来也不是顶冷的。老陈急急地向我走来,他的眼睛燃烧着希望的火,笔直地射向我,是那样骄矜地向我询问:“怎么样,你还不信!光我说不行,这回你可都看见了吧?!”是的,我看见了,看见了。印象是如此强烈。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多少有点恍他,好像突然被光束照花了眼睛似的恍惚。同时,我的心仍然为他沉重:老陈,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的情况,远比你自己想到的严重。你这个——也已经被判处了“死刑”的人!而且,你的临刑期还那么紧迫……但是,这些想法立即被掩埋在我的心中。因为,我害怕它们会冲出我的眼睛。我装作十分轻松地向他点头、笑,快步向他走去。“你看,你看!这些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他兴奋地压低了声音说,“我更有信心了,和它拼!趁着还没有给我判刑。”他狠狠地咬着牙关,神色十分庄重。当年,打仗时,他报名参加尖刀班,大概就是这种神色吧?但现在,是和平时期了。我和陈大姐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过分大声地笑起来说:“对,和它拼!老陈!趁着还没有给你判处‘死刑’。” 癌症明星和其他从此,每周两次,我们风雪无阻地在紫竹院学起功来。两个半月过去,奇怪,我们竟都没有感冒。我的心脏病没有加重;陈大姐没有晕倒,老陈呢?腹部疼痛居然大为减轻了……能说是气功的功劳吗?老陈同时做着放疗化疗。按照传统的观念,当然还是放疗化疗的效果喽!但这里,有一个事实不好解释,就是放疗化疗的病人由于白血球大量杀伤,大都食欲减退,恶心难忍,睡眠不佳,很快就体力不支,于是……但老陈呢?仍然每天迈着他军人的阔步:左、右。左;吸、吸、呼;吸、吸、呼;右、左、右……活像急行军似地操练。一餐仍然吃两三个馒头一碗饭;仍然把三顿正餐中他老婆辛辛苦苦搞来的鸭子、牛肉、排骨、蹄膀……(连我一看见都直犯恶心的诸如此类)连盆带碗地吃个净光。能说都是毅力和信心的作用吗?毅力可以支持他硬吃,但不能制止恶心;信心可以支持他操练,但不能遏止疼痛,更不能在放疗化疗两个疗程之后使他的白血球从低于4,—5,—6,回升,使他的体温从38—37.8一37.2摄氏度下降。而在癌症班里,像老陈这样的,用气功帮助他们支撑度过放疗、化疗关卡的还大有人在。不能迷信,可以怀疑,但却不能不引起每一个尊重事实的人们的注意。在我的朋友小韩的帮助下,我开始阅读起有关的大量材料及报刊来。据北京市肺部肿瘤研究所蔡廉甫等三位同志的文章报导:气功确实能增强肺癌病人的体质,帮助病人恢复体力来耐受放疗和化疗的消耗……(见年7月2日《体育报》)而年10月15日的《解放军报》发表的沙衍孙同志的文章,更是具体地介绍了海政某部高文彬同志运用气功治癌的经过:高文彬同志年8医院开胸后,发现右肺门淋巴腺癌广泛转移。已是晚期,无法手术,只能缝合。之后进行放疗与化疗,他又无法耐受,整天头晕眼花,全身不适,白血球迅速下降……医生断言只能存活半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练气功,坚持两三年,就上班了。人们都说,这真是个奇迹……年7月《成都日报》刊载一个患了乳腺癌切除两年后转移成肺癌的病人万倪雯,怎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郭林治癌气功班的病人,从此,在服药的同时,开始了气功。如今,不但病灶完全消失,而且自己也成了“新气功疗法”的辅导教师。年3月22日的《长江日报》又报导:一个患骨癌的病人在开始新气功疗法后如何迅速好转……材料原来这样多:《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日报》。《新体育》、《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澳门日报》、《科学与未来》……真是摘不胜摘。我开始急切地盼望早日出院,盼望能够亲自走访的时刻,不知不觉地,我练功比以前用功了。在一个朔风凛冽但却阳光明亮的早晨,我们在紫竹院小山后,排成一列让辅导员查功。辅导员于大元不时用夸张的动作模仿学员们不正确的姿势。一会儿说:“唉,你不要抖嘛,腿这样一抖一抖,不像做气功,倒像在跳《花儿与少年》。”他边说边哼着《花儿与少年》的曲调跳了起来:“咪索咪来,咪来都西拉,拉西拉索咪索拉——山上有一朵红牡丹,山下有一个美少年——”一阵友好的哄笑还没有停止,他又指着另一个学员嚷了起来:“你的脖子咋个那么扭哩?那不成了新疆舞了!哎,哎,这样,这样。自然摆动,自然摆动嘛!哎,对了,对了。不然你回去非脖子疼不可……”他突然停止了模仿那个学员的动作,指着我嚷了起来:“你,你,快,快——”,我以为我的动作哪里又不对了,马上转身向他。他却带头鼓起掌来说:“你回头,快回头看嘛,你想采访的人来了!”他又转过头来对着大家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癌症明星来了!”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急忙转过身去,只见一个中等身量,健壮结实的人向我们走来。是的,这就是那个被判处了“死刑”却不甘心死亡的高文彬。各种报纸上为他写了多少文章,电视台也曾专门介绍过他。老学员想必都和他熟,他们兴高采烈地和他打着招呼,一下子围了上去。我四顾寻找老陈,老陈却早已挤入人群的中心。他紧紧握住高文彬同志的手,笑着在叙述什么,高文彬也笑着在侧耳细听。“你比电视上还精神。”老陈说。“谁到了镜头前都会紧张,不信你试试。”高文彬诙谐地说。“我?我可没这一天了。”老陈苦笑了一下,突然压低了声音,“我的腹部疼得厉害呢!”他眼巴巴地望着高文彬,周围立即鸦雀无声。高文彬却笑笑说:“不要紧的,我刚来的时候,几乎路都走不了呢!每次行功顶多走个十来步,就得坐下来歇一阵……”“就是嘛,”老陈的爱人高兴地说,“你比人家高部长那会儿不强多了?!”“我每天练三次功,加起来差不多有两个小时呢。”“好样儿的!所以我说你大有希望嘛!”高文彬笑嘻嘻地拍着他的手。“啥希望,”于大元冷冷地插上来,大家不由一怔。于大元却接下去说:“要是他不增加时间,不校正姿势的话。”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明白了他是正话反说,大家也都笑了起来。“你现在真上全班了?”老陈问。“真上全班的又何止我一个人。”“可原来,不是说你活不过半年吗?”“是啊,我头一年回去复查,医生说:‘咦,——不简单!’第二年去,医生说:‘哎——真是奇迹,’可现在,已是第六年了。”“是医生告诉你——只能活半年的吗?”老陈的爱人急切地问。“医生哪能告诉我,是告诉的家属。对我,医生连长的是癌都不肯说。”他突然不好意思地笑了,“是我觉着不对劲,开完刀,‘情况挺好’。那医生写病历时干吗老用手遮着?我偷偷看了病历,才知道开胸之后,肺癌已广泛转移,不能手术,就缝合了……”“你就马上练气功了?”陈大姐问。“哪里,我那时哪信这个。是做放疗化疗,不到一个疗程却完全不能耐受之后……”“可我能耐受,好像还可以耐受下去。”老陈说。“那是气功增强了你的体质,加大了你健康细胞的吞噬力。干吧,伙计!癌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反正你不吃掉它,它就要吃掉你。”“听见没有?老癌们!”于大元又插上来说,“加劲干,老陈,来日也当个癌症明星。”哦,明星!高文彬当然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他的事迹给了多少苦苦挣扎在病榻之上的人以希望;又鼓舞了多少“老癌们”顽强地拒捕于死亡之门。但于大元竟称他为癌症明星,多么风趣而又确切的命名。夹杂着多少痛苦的欢乐,标志着多么辛酸和艰险的历程:黑暗与光明;绝望与希望;死亡与生命;失败与成功……多少对抗性的矛盾这样和谐地统一于这个充满辩证法的古怪名称之中。于大元是具有四川人的幽默感的。而幽默,又总是来源于力量和信心。我的眼眶一下子润湿了。我不禁一连退后了几步,以便能更好地打量这一群:这一群被癌的王国无情地判处了“死刑”的囚徒;一群被死神紧紧扯住衣襟的俘虏;一群在凡人眼里的活死人!但他们却又是癌的王国里不停抗争的叛逆;一群千方百计打破囚笼的勇者;一群用殊死的角力,一分一秒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的角斗士;一群确是比凡人更多勇敢,更多信念,更多生气的不凡的人!在这殊死的决斗中,他们有的已遍体鳞伤,有的即将牺牲。但他们只要还有一口气,还能走一步路,他们就将继续这一场力量悬殊、几乎是无望的角力,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给未来者点燃希望的灯……哦,我盼望,我盼望——而且相信:从这一群中将不断出现新的明星。最后,将出现一个光辉灿烂的明星群,高高地挂在祖国深远的长空,向全世界宣告:看,在东方,在中国,又升起了一类你们一直在寻找的新星——古老的,却又是年轻的;奇异的,却又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星。但,从现在到那时,这中间还需要多少努力,多少探索,多少血泪,多少生命,多少艰难险阻,多少挫折与教训啊! 数据与活人于是,我又不能入睡了。哦,我可怜的医生同志,又每天为我增加了镇静安眠药的剂量,我可怜的护士小友,又时常被我的红灯惊动。而我可怜的心脏、神经又开始为我备受折磨,并不断向我提出抗议……但我仍然不能入睡。我兴奋,我震惊,我充满看到希望的欢乐,却又为不能捕捉住希望而十分痛苦。我把我看到的、想到的一切热烈地向我的朋友述说,性格温和的朋友微笑着点头:“哦,多么好,但你千万不要如此兴奋。”但更多的像我一样自命为文明人的朋友,则带着科学的态度文雅地摇头:“是吗?这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啦!”“那为什么不见宣传?”我拿出大叠大叠的报纸和材料。“医院不实行?”“医院不是已经同意我们去了吗?”“那为什么不推广?”我生气,我抗争,我辩论,但既然我已不是癌症病人,他们也就不再对我迁就忍让。朋友归朋友,但真理不容含混,我的朋友都是些原则性很强的人。但毕竟我还是病人,于是他们总是那样带着礼貌的微笑听着我叙述。听着,眨眼睛(眼里明明透出怀疑),点头,摇头,但不做声。“你不信吗?”每每我忍不住问。“信。气功吗?怎么不信?”“气功在配合中西医治癌中的作用呢?你不承认?”“可能。”“那你们不能试用于临床?”微笑,不做声。我这才懂得有时微笑也能压迫人。“为什么你们不能用于临床?”“病人自己做,我们不反对,但让我们用于临床,却必须有数据。”数据,什么数据?就是气功治癌的系统科学的理论根据及实验的各种数据。那,我当然没有。而许多气功师呢,也没有,甚至不可能有。如果所有可能去搞数据的人都在等别人去找数据,并且对古已有之及现在做着的那些零星的、片断的数据只持简单的否定态度,那么,还将永远不会有。但是,我有活人。数据不是从活人的实验中统计和总结出来的吗?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动员我的医生朋友们去看活人,大活人。人类总是有弱点的:好奇心,温情,碍于情面……而人类又总是有优点的:同情心,求知欲,事业心……总之,不管优点弱点,我是动用了一切手段,连说带劝,连推带拉,硬拖了几个医生朋友上了紫竹院癌症气功班。这里,我将尽量客观地记录下那些活人与活动。如同邀请我的读者和我们一同前往现场。时间:年12月的某一天。地点:紫竹院旱冰场小山侧的空地上。人物:我们(我,陈大姐,老陈,他爱人)。我的医生朋友们。癌症气功班的学员们、辅导员们。场景:在冬日明亮但不温暖的阳光下,北风吹着枯干的竹丛,飒飒作响,学员们正排成两行做着行功。辅导员在边上喊着“吸吸呼,吸吸呼,吸吸呼,平、点;吸吸呼,平、点……”我:(走近辅导员)对不起,我们今天请来了几位医生,想找几位病人谈谈。可以吗?辅导员:当然。情况你都熟悉了,你自己找吧。(转身走开,仍继续查功)吸吸呼,吸吸呼……我:(走向一个身穿紫衣,围着暗桃色大毛头巾,身材窈窕脸色红润的女子)周月辉,小周,你和他们谈谈吧,好吗?周:(脸一下红了)我?咋说呢?我:就像那天你和我谈的那样,好吗?周:(笑嘻嘻地)我谈不好,你可别怪我啊!(我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并打开了录音机,她仍然笑嘻嘻地,开了口,话说得很快。)——以下为她的录音整理。“我说不好,反正我就说大实话呗!同志们有听不明白的,尽管问我……我叫周月辉,今年42岁。在长春白求恩医大二院工作。五年前,就是年9月20日,由于胸闷,偶然发现胸腔有一肿物。10月30日在长春白求恩医大做了开胸手术,取出10x10x8cm肿物,未发现扩散,但与心包、主动脉、上腔静脉、肺、膈肌广泛粘连。“病理诊断:上皮细胞和淋巴细胞混合型胸腺癌。“病案号:吉医院,医院。“我手术后,为了预防扩散,用混合化疗方案做了十一个疗程出院。“术后近两年,年8月4日,回院复查时,胸部正侧位片子均显示:原位复发。经空气量5rad的钴6o照射,拍片检查阴影消失。我高兴的呀,就别提了。我说‘谢谢,谢谢医生同志!你们救了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命。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我只有做好工作来报答你们……“哪想到癌不饶人呀!一年后再复查时(年10月30日),不但在原部位再度复发,而且扩散到前胸壁和右第二肋间。为了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我跑到北京。医院的医生专家们反复研究,都认为复发严重,不能再做第二次手术,否则很容易下不了手术台。我请求再给我放疗,医院放射科都劝我不要。因为放射面积太大,容易造成放射性肺炎,及造血机能障碍。我再三恳求无效,只得回长春吃中药治疗。“年6月24日再次复查,病情更加严重。这时我已呼吸困难,睡觉不能仰卧,侧卧时间一长,也上不来气,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医院都认为无救了,有的认为存活期超不过年10月。“在豁出去的情况下,我又跑去找第一次给我动手术的四院。找到陈公言主任,我说:‘主任,主任,你救救我吧!我这么年轻,还能工作。我的孩子还小,他们还得有妈妈,你不能就眼看着我这么死。你给我治吧,开刀吧,多么痛苦我都能忍耐。你上次救活了我,这次我死在手术台上也不怨你。不治反正是死,万一治好了呢?啊,主任,主任……’我恨不能给他跪下,医生护士听了都掉泪,可也没办法。最后陈主任决定再做第二次钴60照射。在年7月10日再次结束了空气量5Rad的钴60照射。拍照结果是:肿块阴影似有缩小,但未消失。继续放疗已无实际意义,因肿瘤对第二次钴照射已不敏感,且脊椎已达极量,并出现了胸水……医生垂着眼皮对我说:‘带瘤生存吧,再照不得了。带瘤生存吧,小周,世界上有好些人是带瘤生存的。’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我懂得这个‘带瘤存活’,此时此刻的意思就是等死。我再三恳求再次手术及放疗,但自己也明白这是毫无意义及不可能的了。“正在呼天不应,入地无门,又不甘心就这么白白死去的情况下,我校一院医学运动科的王艾明大夫告诉我:北京画院郭林的新气功协助治好了高文彬同志的转移性肺癌,让我试试新气功。我当时到处也找不到郭林老师的这本书,就按着王大夫说的,先迈右腿——两吸;再迈左腿——呼;舌舔上腭,闭着眼睛走……我就像溺水时有人递给了我一个救生圈,一把抓住可就不放啰!从年8月1日我就走了起来,头一天只能走几分钟,慢慢地就能走半小时、几个小时了。走着走着,能吃下饭了,睡觉呼吸也轻快了一点。呀,莫不是有了希望了?!“走呀!走呀!我活过了‘十.一’。活过了‘十·一’,我就有信心了。在东北零下40摄氏度的大风雪里,你们可不知道那个冷哟!我每天4点起来,就不间断地做行功。走呀走,吸吸呼,吸吸呼。吸吸呼,把氧气吸进来;吸吸呼,把毒气甩出去。大雪飘飘地下,冰碴在脚下‘沙沙’地响。轻轻地碎裂……吸吸呼,吸吸呼,但愿吞噬细胞也能像白雪这样密密地扑向癌细胞,但愿肿瘤也能像冰碴这样被包围、被掩埋、被粉碎。吸吸呼,吸吸呼……“练了六个月功,到年2月13日又拍片复查,拍完片,我扭头就往家跑,都不敢问结果。“吃过中饭,我爱人‘扑通扑通’地跑进屋,脚步咋这么重呢?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一动不动地等他宣判。他却老也说不出话来,就像喘不过气来似的,我心想这下子可完了。谁知他大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有了,胸骨后的阴影——没有了。消失——了。’我像作梦一样听他说,是我院放射科赵楚静副教授给诊断的。‘刷’地一下,眼泪就‘咕嘟嘟’地从我眼里往外冒。“他这会儿也不结巴了,话像开了闸,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医生怎么抢着看这张片子啦;什么都不敢相信啦;什么就剩二肋间那个还有啦;什么什么……我可都听不进去了。站起来就抓个包,拉扯几件衣服,二话没说,拎着包就往外走,上北京,上北京,上北京哟!“到了北京,进了这个班。这一正经学,这才知道,我的姿势还不大对呢,光知道在东北大雪地里傻走,原来还没有做预备功,也没做收功哩!哈哈哈……”她爽朗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我们也高兴地大笑起来。我一边扬声大笑,一边小心翼翼地用眼光骄矜地查看我的医生朋友的反应,倒好像给周月辉治好病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我一样。咦,怎么听不见老陈那轰轰的大笑声呢?半晌,我忽然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忙回头找时,原来他的爱人抽抽噎噎地在一边抹泪儿。若陈拉着她的手,直说:“咦,你这人,你这人,真是——哎……”我的心一热,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了。“做过切片吗?”医生到底是医生,冷静的调查开始了。“做过不止一次,我病历上都有。门诊号……化验单……”“这半年——就是年8月到年2月,做气功时,你还进行了放疗或化疗吗?”一个医生问。“没有。”“还进行了别的治疗吗?”又一个医生问。“只注射过中药蟾蜍素,这是一直没停过的。”医生点点头,不问了。我却问道:“会不会是放射线在继续起作用呢?”周月辉笑了:“不。陈公言主任他们研究时还专门说过,钴60照射停止一个月后,就绝对再起不了杀死癌细胞的作用了。因此,他还开玩笑地说:‘你的阴影消失,我决不冒领功劳……’”那么,是蟾蜍素的功劳?但以前也注射过,为什么偏偏这半年间它起了作用呢?我又小心翼翼地看了我的医生朋友们一眼。哦,数据吗?我没有!活人呢?我多的是。我打算带他们去找一个我熟识的老同志徐政委。我认识他可不是在癌症班,但我们这次相遇却是在这个癌症班。年,我听说徐政委得了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让“四人帮”及其爪牙气的。医院看他,手术很成功,他也十分乐观,送我们出门,还一边走一边说笑。但去年听说,已转移到肾和肺,不行了……我心里十分难过,躺在病床上还想着他曾经对我有过的帮助,想着在“四人帮”横行时我们去到山西,曾经带给他的种种麻烦……可惜现在医生限制我的活动,无法去看他了。万没想到,一天我来紫竹院学功时,突然看见一个老军人正在我前边慢步行功,一招一式,十分沉稳从容。我不禁跟在后边摹拟,越走越觉得这人似曾相识。我学功还没入门,从来很难入静,这时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谁呢?究竟是谁呢?我终于追到前面,细细打量——啊,原来是他!虽然因为清瘦多了,有些改了容颜,使我没能立刻认出他来,但更主要的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活到今天,还站得起来,还在这儿从从容容地吸吸呼,吸吸呼……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快步追了上去,高兴地轻轻地喊:“徐政委,徐政委——”,他回过头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听说你也病了……”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恍惚间,不知怎么颇有点隔世之感。此刻,我急着在人群中找他,但却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显然对这类访问,他早就习以为常,不需要听也不想多讲。我放目四望,只见他的背影在小山后一闪,迅速地进入到小树丛中去了。他是在快步行功呢,步履仍是那样沉稳从容,就好像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但他走得好快呀,又像个急于夺取胜利的小兵在勇猛冲锋……他哪里像个病人?!联想到这个癌症班的学员每天到公园来练功时,经常在公共汽车上给妇孺老残让座的故事,我不禁又破涕为笑了。可是数据,数据呢?数据吗?周月辉在轻轻拉扯我的衣襟,带我们走向了一个穿粉红色罩衣的姑娘。她,容长脸儿,细挑身材,27岁,尚未婚。26岁时,乳腺癌全切后一年复发,广泛淋巴转移,也是没有可能再做手术及放疗化疗,只能等死的……现在做气功八个多月了,颈淋巴上的癌肿块明显变软变小,从核桃大变为花生米粒大。左右肋淋巴结原来一串串花生米粒大的肿块,现左边已缩小;右边嘛,已完全消失……做过切片吗?当然。病理诊断……门诊号……住院号……她还那样年轻,还没有结婚。在回答我们问话时带着那样明显的女孩子的羞涩。因此,请原谅我在这里不引用她的姓名了。我带着我的医生朋友们又走到一位黑黑胖胖的男同志面前,请他讲讲。为什么我找他呢?因为我刚来到这个班时,他曾一次拦住我说:“听说你是个记者?报导报导吧!”我说我不是记者,只是个病人。他遗憾地打量着我说:“那我怎么听说你是——唉,真该报导报导啊!”此刻,我把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他立即高兴地说起来。“我早就希望能够报导报导了。当然,不是报导我,而是报导气功,郭林老师的新气功……“我是肝癌,在河南确诊的。医院就多了,都说确诊是肝癌。到北京,又跑了好医院,也都支持河南的诊断。有诊断书嘛!我自己也看了片子了……肝上,有拳头那么大,都说已无法手术,告诉家里人活不了多久了,想吃啥就给做点啥吧……吃啥哩,啥也吃不下。老婆哭,孩子叫,这就都不用说了……“你们看我现在壮壮实实的,吃得可胖了。可那会儿呀,真瘦成了人干了。怎能不瘦哩?不吃不睡,就像点灯耗油一样。”“我虽只是个普通干部,在河南XX合作社工作,但咱从小参加革命,好歹是个老同志,是个共产党员。再疼得难熬,疼得不能活,也是最后的考验了。我就去照了标准像,召开了家庭会议。我说:‘我们都别哭了,哭也不能把癌哭没了不是?摊上了,有啥法哩!我也五十多岁了,比起早牺牲的同志,还多捡了几十年哩。共产党员嘛,啥考验没经过,在死亡面前也得脸不变色心不跳哇卜……我也没啥可留给你们的,就是留给你们这点不怕死的精神吧。标准像,等我死了就挂上几天,留个念性。尸体呢,送去解剖。把癌这个玩意儿好好叫医生们研究研究,要能叫后人少受点疼,也算我没白长一回癌病吧!’“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组织上、同志们纷纷给我找来了气功治癌的报纸、郭林老师的书,劝我上北京,找这个癌症班来学气功……我就半信半疑地来了。“来来回回练了这么一年多功,现在,你们看,我有多胖。X光片上什么肿瘤的影子也没有了……没了。你们说,神不神?”他正在滔滔不绝地说气功的好处时,一位医生打断他问:“做过切片吗?”“没有。当时所有的检查都支持是癌。在肝上那样大,都说手术愈后决不会好。都说不挨这一刀,可能存活期还长点。”他扫了医生们一眼:“哎——我知道,你们会说,没有切片,就不能证明那是癌。是的,我一好了,片子上一没有阴影了,我只一说没动手术,是气功治好的,医院顿时就说是当初误诊了。医院都误诊了呢?还是不相信气功能治病呗。咱是不懂医,可你们大家琢磨琢磨,退一万步说,就不是癌,是个良性瘤,是个囊肿,那么老大个家伙,就这么吸吸呼,吸吸呼地给吸得不疼了,呼没了,你们也该研究研究吧!否定一件事咋那么容易,肯定一件事咋那么难呢?我也懂,要数据,要数据,可不研究,不积累,死了才是癌,一好了就说是误诊,这数据从哪儿来呀?”他的话说得那样朴素,又那样在理,许多病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了,眼光期待地射向在场的医生同志。他们都是病人,重病人,死刑犯!医生决不会和他们争辩。她们只是宽容地笑笑,什么也没说。我也什么也没说,但回来就抓住她们不放了。你们看见了吧?相信不相信?难道是假的吗?可能个别有例外,原因不好解释,那你们为什么不寻求解释呢?怎么寻求?做试验呗,找数据呗……但是,我也知道,这不可能。首先,他们忙,真忙。是的,真忙。谁要是没有在80医院里看过普通门诊,住过普通病房,谁就不会懂得中国普通医生的忙。那甚至不是忙,而是劳累,是不能喘息。门诊,每个钟头4——10个。询问,主诉;听诊,门诊;化验,透视;照相,分析片子;解释,答问;开方,处置,写病历……住院医生呢?每天工作平均不下10个小时:早班,晚班;大夜班,小夜班;治疗,查房;急救,抢救;开研究会,碰头会,学习会,讨论会;开诊断书,病历摘要,出院证明,死亡证明……当然,还不算排队、走路、挤车上下班的时间……你怎么还能要求他们考虑治疗外的事,做什么试验呢?其次,他们无权。他们只是普通医生,他们没有权利拿教科书上没教过他们的理论、没有足够科学实验数据的任何方法用于临床。我没有话说了,但我的心并不平静。是的,他们没空。那么,有空的人呢?专门研究的人员呢?是的,他们没权。那么,有权的人呢?有权而又专管医学科学的人为什么不组织这项研究呢?是的,需要研究的项目多得很,但为什么这项就命中注定不该早日排上重要日程呢?我确实不懂,并且因为我确实无知,不知道这些应该归哪里管。因此,请原谅,我决不是想把矛头指向哪个单位或哪些人。我只是想说,牵涉到这么多病人生死存亡的最凶恶的敌人——癌,难道不需要组织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制服它吗?为什么只能走西医西药的道路,而不能从祖国医学遗产中(包括气功)更广更深地去挖掘呢?从前节所提的肿瘤研究所的文章中知道,有些专门人才、专业机构已开始在做了,但为什么不能更广泛更普遍地做呢?譬如,医院的肿瘤科,肿瘤研究组,为什么不能和这些癌症气功班挂起钩来,在统一的指导下,配合作战,积累经验,从而取得数据呢?数据,啊,数据!数据是重要的,但活人毕竟是根本。没有活人,没有和活人关系最紧密、接触最频繁的临床单位,不相信发生在活人身上手术以外的“奇迹”,不研究活人取得奇迹的一切条件。一切因素和一切可能,什么时候才能掌握足以说明问题规律性的数据呢?而病人不能等,因为癌症不肯等啊!于是,成批成批的活人,有的是我们至亲至爱的人,有些是对“四化”大有贡献的人才,甚至是栋梁之材在被癌症吞噬。这个该死的、万恶的、必须迅速征服的癌症啊! 北京治疗白癜风的费用白癜风初期治疗方法
- 上一篇文章: 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再论医学与科学上
- 下一篇文章: 国内首家造口病房在北京肿瘤医院国际诊疗中